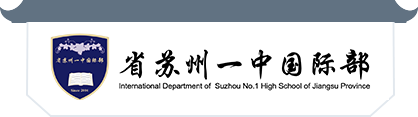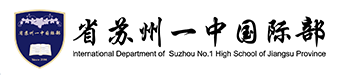留学美国 在美国这半年
作者: 发布时间:2011-07-27 阅读次数:101

张陆陈,苏州中心美国班 东北大学电子工程(获东北大学5000美金奖学金)
2010年夏,初到美国的时候,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而陌生。由于当时是和朋友同行,所以这份陌生感变得那么微不足道,也着实有着一种前来旅游的奇异心境,感觉我并不是要生活在这里,而只是路过。
然而如今,在过了6个月之后,同学都早已离开,去往自己的大学,当周遭的环境由陌生转为熟悉,我才慢慢觉得自己在这里学习生活的这个事实,充满着立体化的真实感。
总结概括为:独而又不独。
张陆陈在实验室拍摄的照片
在美国的学习,就我个人而言,节奏紧凑程度和心理压力大小,与在高中时期的状态十分相近。
唯一不一样的,就是在高中,课间总有甚欢的交谈和吵闹,而在这里,教授一说:“Ok, I’ll stop here.” 所有人都是拿起书包就推门,匆匆忙忙地奔向另一个教室。以至于上了半年的课,同一教室里的大部分人,都是互不相识的。要是路上遇见了,也就点头微笑一下,以表寒暄。
这种“独”在一开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,因为这和我来美国前所想象的同学关系并不相符。
我以为可能是由于我是国际学生的缘故,想要融入集体中并不容易,所以才会产生这种尴尬的生疏感,久了以后才发现,美国学生互相之间,也是如此。
在我看来,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美国大学的“独”文化,而我也深陷其中。
大二的课程明显比大一更加充实紧张。9门必修,一周15节课,从周一上到周五,基本上每天9点上课,下午3点下课,偶尔的实验课做到5点。每周四门主课小考,两个期中考试,一个期末大考。
从学期开始到现在快结束了,我总感觉自己有一根神经一直绷直在脑袋里,不停地鞭策自己。就像刚刚喘了没几口气,又得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走。
很明显,在这种情况下,“独”成了一种必然的方式,给予自己足够清净的空间,来慢慢地消化课业。总要一个人去图书馆,一个人看书,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匆匆游离在教室之间。所以,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交朋友,去Party,去social。常常要一个人锁在宿舍,外面是舍友在放poker face,我在里面奋力地写电路作业。学会“独”,让我获得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,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怎么安排妥当。
但是“独”并不是要求自己与外界切断所有连接,不是像得了自闭症一样的缄口不言。在美国学习生活,也有很多“不独”的地方。
比如上实验课,在动手做实验的同时,必然要和同组的同学交流讨论,必然会有疑惑的问题要向助教请教。然而就是在这种交谈中,潜移默化的,自己已经融在这个圈子里,与别人进行着互动。而在这其中所获得的信息和知识,也远远超过了那些黑板上苍白平铺的板书所传达给我的东西。
与笔记看对眼,和与人相交,显然后者来得更为生动而立体。
另外,美国大学令人眼花缭乱的社团活动也是把自己从过分“独”的状态中释放出来的一种方式。
当然没有可能一下子参与四,五个社团,不然不只自己搞的精疲力尽,头昏眼花,拖扯学习效率,还可能几个活动都参加的有始无终,犹如蜻蜓点水,程度浮于表面而无法深入。到最后,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了什么去报名,只是徒增数量,而不见质量了。
我选择了活动地点离宿舍较近的intergroup dialogue。每周一晚上一个小时,八,九个同学围坐着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自己的看法,分享自己的经历。由于国籍,背景,取向不甚相同 (我的小组里有来自印第安,瑞士,英国,法国,比利时和德国的同学,还有同性恋者),在对同一问题的观点上也有不同的立场,这拓宽了我的认知角度和范围,而我也经常被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想法所惊触。每次的活动,交流气氛都异常轻松,似茶余饭后的闲聊,乐趣无穷。
我也常常去听电子工程社团举办的每周讲座,主要请部门里的教授讲他们研究的领域,或者是一些最新的科技导向。每次听完讲座,我都觉得,自己和专业的联系紧密,而且充满着激情和动力去探索创新。在这个被机遇充溢着的大学里,我好像迫不及待地要伸手去抓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“不独”让我打开门走出去,接受阳光,让我找到细腻的生活,找到充满血性的大学生活。
但是,在美国读大学,“独”与“不独”这扇“门”的开合,全掌握在自己手中,没有人帮你来做决定,所以这其中的权衡与思量,也应受到十分的重视,不会随性开之闭之。
美国半年,磕磕碰碰的很多,但是自身在其中的变化虽然难以言表,确是极有收获的。而至于“开门”“关门”的正确时间,我也还在继续摸索之中。